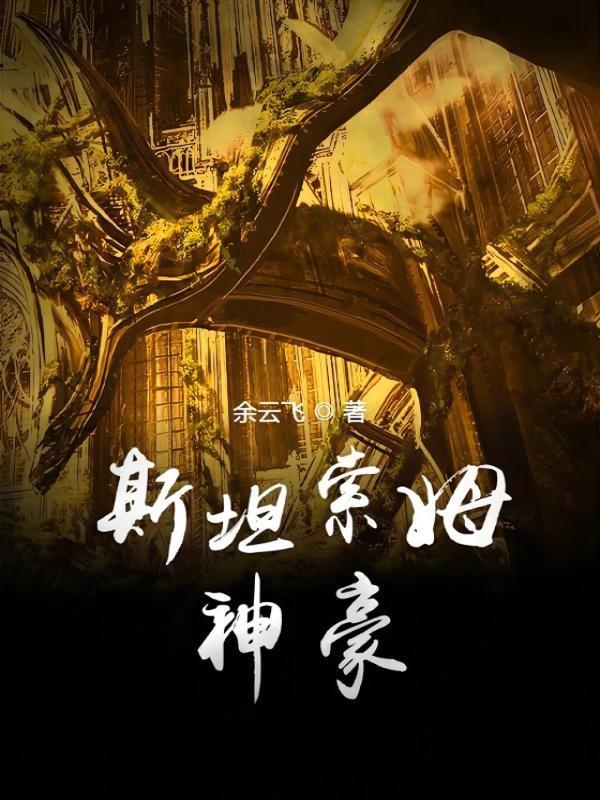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2(第1页)
2
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三日,一个平淡的、既无奇灾亦无异象的日子。当日前后为雨水节气,象征着人间时日开始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人如草木,又不及草木。草木没有虚妄心,人有;草木抵得过一个王朝的坚固长久,人却抵不过一世枯荣。所以说,人比草木脆弱。那段日子里,北京城里的官员士大夫和老百姓最大的谈资,无非是奕被免去议政王及一切职务。奕不是旁人,是那个在辛酉年(1861)里,凭一己之力将慈禧送上青云之巅的男人。奕下台了!没有比这更值得让人嚼舌头根的事,各种版本的传言飞来飞去。天子脚下说起宫闱秘辛,就像是在说胡同里的那点事,过的是嘴瘾。
那一天,谭府上下也忙得不可开交,又添男丁,此男丁便是谭嗣同。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外烂缦胡同。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也即“懒眠胡同”。菜市口地区是彼时京城的交通要道,蛛网交错,南纵北横,而烂缦胡同便是其中一条。这里地方会馆林立,像一颗颗棋子散落于胡同。行走于此,经常会有南腔北调的官话不知从何处传来。清人赵吉士描述:“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六个会馆,其间花团锦簇,煞是热闹,故改此名。
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面前,人是第一要素,而要使一处建筑焕发活力,就必须不断地及时寻找他的主人。所谓有主之物,看的是主不是物。主人的声名,要能够超越金石之坚、砖瓦之固。不然,人朽,物也随之湮没。谭嗣同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时运使然,人奈何之。惊鸿一瞥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仿佛命中注定,却又令人不胜唏嘘。在谭嗣同前已有兄姊四人,均为徐氏所生。因其于祖父谭学琴谱内行七,被称“七公子”。在谭嗣同的童年时代,母亲徐夫人对他的影响最大。徐氏深受传统礼教的熏陶,把服侍丈夫、抚养子女和管理家人作为自己的唯一责任,属于旧式贤妻良母式的中国传统妇女。
谭嗣同在他的自述中,每每触及先母,都会惊颤和痛惜。他写道:“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蔓操笞不少假贷。”旧戏文里的母亲好像用了同一张面孔,不知她们是因为做了母亲才这般,还是因为她们是女人,生来便如此这般。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可又不一样。在时代的缝隙里,她们是灰扑扑的影子,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可是在谭嗣同心里,他对于母亲、姐姐们,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闰,始终抱有怜惜之意。谭嗣同深情地回忆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先夫人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她对子女寄予厚望,如果违反家风、礼节,她会严厉训诫。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小事,她也会恰当地给予指引。她经常当着儿女的面说起自己所经历的贫苦往事,让子女知道衣食无忧的生活来之不易。在那篇写给母亲的祭文中,谭嗣同把徐夫人描述为一个勤于吃苦、不苟言笑的严母,孩子们犯下过错,她会毫不留情地体罚。
以至于谭嗣同读书时,内心对于老师所说的父严母慈一说,存有深切的疑惑。母亲的教育极为严苛,她完全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遵守祖父开创的谭氏家风。这个深受伦理法则影响的女人,又用这种伦理法则教育子女。她要求自己的儿女,既要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要不忘社会责任。徐夫人的言传身教对谭嗣同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得他们虽然出身官宦之家,贵为公子,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中国人的性格养成,通常是扁平式的积累过程,与巍巍然的伦理相互成就。母亲灯下劳作的身影,与人为善的品行,性格上的坚毅,所有这些构成了谭嗣同的性格史。
母亲,通常是我们生命天空里恒定的北极星,她的光芒,指引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从谭嗣同记事起,母亲忙碌的身影便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父亲在朝为官,收入颇丰,本不需要母亲如此辛劳。可他的母亲根本就不像一个官太太,甚至还不如浏阳城里地主乡绅的大房小妾活得安逸。餐桌上从来都是粗茶淡饭,每餐不超过四个菜。身上穿的布衣虽然洁净,但补丁摞着补丁。一日,家塾先生闻得一墙之隔,纺车轧轧,彻夜不休。第二天,先生就问谭嗣同:“你家的婢女用人如此辛劳?”当谭嗣同告诉他是自己的母亲时,家塾先生大为惊叹:“你父亲在朝为官十余年,位居四品,你的母亲却没给自己放松享乐的时间。如果你们嬉戏惰学,不思进取,又怎能做到心安?”
从那以后,谭嗣同变得愈发勤奋。每当怠惰偷懒时,机杼声便会在耳边响起,让他不得安宁。他不仅白天用功,晚上也温习功课。琅琅的读书声和母亲摇动纺车的轧轧声交织在一起,如同优美的夜曲。如果有可能,谭嗣同宁愿像母亲那样,做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自食其力者。
谭嗣同七岁那年,他的大哥嗣贻娶浏阳黎氏之女,徐夫人挈长子返浏阳完婚。因路途遥远,旅行不便,遂将谭嗣同留在北京。临行之日,谭嗣同和家人到卢沟桥为母亲送行。这是他第一次远别母亲,谭嗣同强忍泪水,默然无言。那时的他虽然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却比同龄人情感来得浓烈。母亲走了好远,回头看他,他仍站在那里不肯离去。母亲离开后的一年中,谭嗣同思亲难抑,生了几场大病,形容消瘦。待到第二年母亲回京,看见他瘦骨嶙峋的样子,不由心疼,问他是否想念自己所致,他却想到当初与母亲的约定而矢口否认。不苟言笑的徐五缘也被儿子乖巧惹人怜的模样逗笑了,颇为欣慰地对旁边人道:“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
徐五缘嘉许了儿子,这个倔强自立的女人将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投射于儿子。你若自立,我便死得安心,她用极度的不安全感勉励谭嗣同自立。谭嗣同后来养成的一身傲骨皆源于此,而凡事易张难弛也变成肌肉记忆存储于他的身体。无论何时,谭嗣同始终保持着一种孤身立于危地的凛冽之势。
母子间其乐融融的温情画面,永远都无法定格。随着父亲谭继洵地位的不断攀升,谭家内部原来比较简单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时的封建官僚和商贾,都有买妾的风气。《李兴锐日记》中就有谭继洵为李找妾的记载:“敬甫知余将置妾,而择年在二十五岁上下。适有送婢求卖者,敬甫邀余一看,遣之去。”置妾不同于娶妻,带有浓厚的买卖性质,妾的出身也往往比较低下。置妾,大多时候置的不是情感,而是门面。科举的成功使谭继洵获得了入仕的资格,意味着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而与之相匹配的享乐成本也水涨船高,纳妾算是功名之士的标配。更何况还是京官,生活上的配置更是马虎不得。马配鞍,剑配匣,辜鸿铭说的“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说的是同样的道理。将女人物化,是那个时代最丑陋的部分,值得用一万吨的文字去批判。
谭继洵到京城为官后,像大多数官僚那样,开始忙着为自己置妾。他完全不用顾及家中发妻的感受,此等境况,谁也说不出什么。而那些在私人生活上无所作为的官员,反倒成为世人奚落的对象。仿佛他们纳的不是妾,而是一件披在身上的华美锦袍,如同插在功名躯体上的一面旗帜。肉身,就像是他们养起来的一件玉器,玉不离身,身不离玉。反复擦拭,日夜揣摩,养出油腻。
成年后的谭嗣同念及母亲,总是愁肠百结。一个女人苦心经营的家庭氛围,在现实世界里不堪一击。她只能像剧情陡变的家庭剧里的女主人那样,保持忍辱负重而又沉默的姿态。同治二年(1863),徐夫人带着子女辗转数千里,从浏阳乡下来到北京。而此时,谭继洵已娶直隶顺天府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女子卢氏为妾。卢氏年方二八,比谭继洵年轻二十四岁,他成了谭氏的第一房侧室。在谭继洵所娶四妾中,卢氏年龄居长,聪慧明秀,很快便为这个家庭添上一子,得到谭继洵的宠爱。同治十一年(1872),谭继洵又娶四川女子张氏为侧室,张氏也生有一子,名嗣。在谭家,卢氏与张氏分别被称为“大姨太”和“二姨太”。
古人有言:“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旧时纲常伦理,面目板正,寒气太盛。小妾在旧式家庭里的地位较低,按照旧制,“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并规定不得以妾为妻。大红灯笼高挂处,人的心思,密如浮埃,身在其中,谁又能逃脱哀愁。妻妾、嫡庶之间的倾轧,有时会异常尖锐。于是,有些家训中还将此录入其中:“素相敬爱之伉俪,因妾生嫌,渐至反目。妇已有子,自可毋庸置妾。先贫后富、先贱后贵者,尤所不宜。”谭家情形也不例外,谭继洵与徐氏算是贫贱夫妻。谭继洵功名无成时,徐氏与他患难十余载,后又随其迁来京城十余年。一个女人能够付出的,徐氏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谭家。然而经此变化,夫妻之间难免龃龉,感情日渐淡漠。
谭继洵宠爱他的小妾,徐氏自然受到冷落。浏阳会馆里经常会传出徐夫人与卢氏的怼怨声,恨屋及乌,两人间的怨怒很快便转嫁到子女身上。徐夫人在世时,卢氏尚有忌惮,不敢过分造次。谭氏夫妇及妻妾之间的不和,使年幼的谭嗣同置身于幽暗的气氛中。人虽幼稚,却心有不甘,常常生出戾气。人生最初见识到的争斗与凶险,便是屋檐下的亲情。家庭生活对于孩子来说,一饭一蔬,一敬一怒,温润人心,也摧毁人心。谭继洵在京师户部任职十七年,正值“同治中兴”时期。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轮番冲击,大清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谭继洵所在的户部是中央政府管理全国户籍和财政经济的机关,在太平光景里,当是京官们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可是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财政枯竭,又当别论。
谭继洵虽然不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但他身上背负着家族的厚望。或许是苦难的打磨,让他对世事人生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谈农政于理财之日,谈榷政于兵燹之后”,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官场就是一个文人最后修炼的道场。谭继洵是个务实之人,处世谨慎,行事稳重,非常人能及。拆东墙补西墙的职务,看上去像是在收拾烂摊子。可是对谭继洵来说,却是最合适的角色。他在户部衙门担任农曹时,曾于人前慨然曰:“农曹者,度支所总,国用民生所系也。”
即使做个不入流的七品小官,谭继洵也要让自己做到熟悉掌故、通达机宜、恪守本职。为官,本来就是为人之道。官场混沌,人神鬼魔共存,但官事还是人心镜像,有一套既定的生存秩序,终途还是明心见性。事实证明,一个心细如发的人,通常要比那些粗枝大叶的莽夫更懂得因势利导地解决问题。谭继洵有着高远的政治理想,小小的农曹职位怎能匡定他的才华?他日夜用功,光是专业书籍就储备了数万卷,同时又多方搜集舆论,了解时势,很快便达到了“博综掌故,精熟食货”的程度。在今日之我看来,谭继洵用儒学理想来度量并不合乎理想的时政,是值得怀疑的。而在彼时的谭继洵看来,他所做的,乃理所当然之事,不止一个循吏和名儒曾经这样做过。大学士翁同评价他“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喜欢按部就班,凡事不愿为天下先。一个中规中矩的、以君子自期的文人士大夫。自适其适,适得其所。在多数人的眼里,他们是没有棱角、谨小慎微的官员。
自古饭碗难捧,君子忧道亦忧贫。一身才华换不回三菜热汤,并不是稀罕事。谭继洵的境遇还过得去,为政既不混沌,也算不得清简。十余年间,他先后在户部下属八旗现审处、井田科、捐铜局、收铜局、捐献局、军需局等处任职,他几乎将户部机务尝试个遍。同治十一年(1872),升补户部山西司员外郎,两年后,又升补山东司郎中。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谭继洵奉旨简放坐粮厅监督,驻北京以东通州。直隶通州向来为南北漕运的终点,每年数十万石漕粮在此交卸入仓,以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供应着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是京师之地与经济重心区域构成空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办理漕政事务虽然劳体伤身,但也是肥缺,其中营私舞弊、贪污中饱乃常有之事。谭继洵在坐粮厅任上,连续三年因办运出力而受到嘉奖,奉旨专以道员用、赏加二品衔。
谭继洵任职通州不久,全家随之迁往北京以外四十里的通州城。此时,次女嗣淑已于几年前嫁给广西灌阳进士、翰林院编修唐景崶,随唐家住在京城;长子嗣贻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举人;而嗣襄、嗣同仍随欧阳中鹄在家塾读书。看到孩子们上进,谭继洵非常欣慰,对他们的教育也愈发上心。月色昭昭,谭家儿女读书喧哗的声音遥遥传来,大地似乎有一种朦胧的回音。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羽飘零
- 我的爆乳巨臀专用肉便器王苗壮(LIQUID82)
- 糜烂病(gl骨)醍醐灌顶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季寒声沈清璇于春色暮晚相拥结局+番外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优雅迷人的金发大小姐奥黛丽和冷艳无口的木偶小姐莎伦被壮汉破处奸淫,最后双双恶堕为淫纹性奴凝夜紫
-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
- 都市奇缘易天下
- 直播也能挽救用品店吗啊若
- 无限之生化崛起三年又三年
- 高贵美艳的丝袜舞蹈老师妈妈(无绿改)江
- 在三无冰龙娘的诱惑战下逐渐染上败北射精癖的冒险者听雨
- 将警花妈妈调教成丝袜孕奴佚
-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为了治疗丈夫的勃起障碍,只好和儿子上床的教师美母大龙猫dalongmao
- 黄历师石头羊
- 【黯的旅程】魔枪舞姬的初体验逛大臣
- 软香(1v1)h苏玛丽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甜秘密(校园高H)翼山明
- Kiss Me if You CanZIG
- 大奉打更人之佛陀的阴谋对酒当歌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江湖孽缘(修订版)红绳紫带
- 名义:人在军阁谁敢动我孙儿同伟好溪之澜2025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我有九千万亿舔狗金(系统帮我睡女人/系统帮我开后宫)番茄第一帅哥
- 四合院:我在四合院有个青梅竹马梦想车厘子自由
- 月明星稀月明星稀
- 亲爱的小孩(母子h)一条孤狼
- 我的卡牌后宫我想躺平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仙子的修行k
- 陈斌高婉君绯色青云陈斌高婉君后续+完结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叉
- 真搞熟妇亲人呸
- 二次元催眠调教日记月
- 仕途佳人仕途佳人
- 官路美人迎风笑
- 乱伦天堂黑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女神攻略调教手册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仙母种情录欢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我和淫乱后宫们的ntrs性福生活chuya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北境之王:穿越后被战神娇宠了+番外看风也听雨
- 裴总捡回来的小可怜,又疯又粘人酒酒子琪
- 快穿之打倒重生文女主露娜斯朵芮
- 谁家小鱼快来认领+番外云边鹤
- 仙子破道曲漆黑烈焰使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综漫同人)拜托你了,银时老师水云烟霞
- 上错暗恋对象的迈巴赫/只有烟花知道八月糯米糍
- 故旧新逢观然
- 头七见魂CPwinter酱的脑汁
- 婚内暗恋[先婚后爱]黎纯
- 鼎炉秘典:道途淫靡长生欲道
- 秋天不回来-我的教师美母江风夜话
- (综漫同人)完美反派就业中[综]天涯晨曦
- Re:从零开始的基沃托斯恶堕计划Arch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黑莲花今天也在碰瓷我薛不会
- (古典名著同人)孙悟空三打奥林匹斯山沈镜渊
- 我的学氓魅魔女友kkkf
- 快穿之差点被带偏了+番外爱吃花生酱烧饼的犰弘
- 男子高中生不会梦到阴阳双胞胎姐妹一盘没有梦想的鱼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梦中攻略室友她哥后,意外掉马宁昏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灵能同人)穿到老公少年时+番外流浪板栗
- 替身罢了,重逢为何不放手无极烟火
- 爱过,但我选权力枕上灯
- (天国大魔境同人)命运引领我走向你+番外流浪板栗
- 重演CP放野燈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白首与君同时间在看
- 死遁后我成了仙门白月光纯情母猪
- (少女漫同人)我的男友是邪脑科学家兔子饼干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