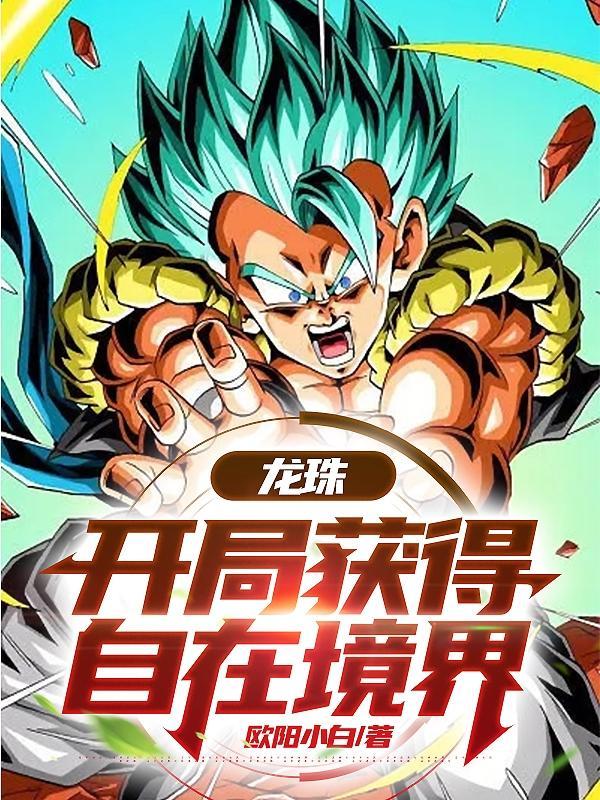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辑 钱书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的评论(第1页)
第三辑钱书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的评论
钱锺书对陆游诗英译本的评论
1946年,英国汉学家凯德琳·扬(ClaraM.dlinYoung)出版了她的英译陆游诗集《陆游的剑——中国爱国诗人陆游诗选》(TheRapierofLu,PatriotPoetofa),配有生平简介性质的导言与陆游年表,并由桃乐丝·路特富德(DorothyRutherfurd)作序,收入伦敦约翰·默里(JohnMurray)出版公司“东方智慧丛书”。钱锺书:《批评札记三》(CritioticeⅢ),《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333页。早在1933年,凯德琳·扬曾于同一家出版社出版《风信:宋代诗词歌赋选译》(TheHeraldWind,translationsofSungDynastyPoems,LyridSongs),并由胡适作序。
《陆游的剑》面世后,钱锺书撰写了长篇英文书评,发表在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1946年12月第3期。
在这篇书评中,钱锺书对中西方陆游研究者过于突出其爱国志士的情怀气概而无视其稍显市侩的一面,提出了犀利批评,也毫不留情地挑出了译诗中存在的大量错谬,有些简直可以当作译林笑话来看。例如,《雪中忽起从戎之兴》的“桑干”,本指桑干河,却被译作“枯萎的桑树”(witheredmulberrytrees)钱锺书:《批评札记三》(CritioticeⅢ),《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3—344页。;又如,《关山月》中的“朱门沉沉按歌舞”,本指边庭守将的官邸深处,伶人载歌载舞,却被译作“残破的,残破的,红色门唱歌,跳舞,演出”(Ruined,ruined,reddoorssinging,dang,ag)《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2—343页。,令人捧腹。其中“桑干”之误为“枯桑”,正如“银河”(MilkyWay)之误为“牛奶路”,堪称中英文相互误译中的绝配。
在批点凯德琳·扬的译艺,揭示她对中国古典诗词审美形式的陌生及对陆游形象的片面解读的同时,钱锺书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旁征博引,兼采多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辛辣而风趣地阐述了他对陆游的诗艺、人格及后世影响的多方面看法,其中陆游形象的单一化、陆游的人性弱点、陆游诗的主题及分类标准等话题,尤其值得关注。一剑气诗心:爱国诗人的符号效应
在书评的开头,钱锺书颇为俏皮地玩味了一番“陆游的剑”这个书名。劈头第一句是,“这书名太有想象力了吧?”(Whythisfancifultitle?)《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3页。随后调侃说,这样的书名类似一个不起眼的便士变为两个光鲜便士的把戏,不过,陆游确实常以剑客自许,而且对自己年少时的英武神勇念念不忘。在陆游的诗中可以找到多首以剑为题材的诗作,最奇特的一首描写某一晚梦见一把闪光的短剑穿过右臂直刺前方,不知道弗洛伊德学派对此作何解释。奇怪的是,陆游的这些咏剑诗凯德琳·扬一首都未选,也许对她来说,剑这种武器只是尚武精神的象征,就像19世纪德国爱国诗人吕克特(FriedrichRückert)将他的诗集命名为“披着盔甲的十四行诗”(geharnischtesoe)。《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3页。
钱锺书统计指出,凯德琳·扬一共选译了四十多首陆游的诗作,其中仅有九首爱国诗篇,而且还有两篇绝非尚武之作。《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3—334页。就是在这仅有的七首尚武之作中,也只在《闻虏乱有感》一首中出现了“剑”的意象:
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
玄熊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
有时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泪如雨。
头颅自揣已可知,一死犹思报明主。
近闻索虏自相残,秋风抚剑泪汍澜。
洛阳八陵那忍说,玉座尘昏松柏寒。
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装何由穿袴褶?
羞为老骥伏枥悲,宁作枯鱼过河泣。陆游:《闻虏乱有感》,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346—347页。
此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九年。当时传闻金廷内乱,各部相残,诗人闻讯后,在猎猎秋风中手按利剑,老泪纵横(“近闻索虏自相残,秋风抚剑泪汍澜”《钱锺书英文文集》中将“秋风抚剑泪澜”一句中的“澜”误为“汛澜”,第334页。)。此时的诗人年近半百(“儒冠忽忽垂五十”),血犹未冷,依然渴望从戎报国、战死沙场(“一死犹思报明主”)。凯德琳·扬将此诗的题目译为“OnHearingofDisorderamongstthePrisonersofWar”《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3页。,又将“头颅自揣已可知”“秋风抚剑泪汍澜”“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装何由穿袴褶”三句分别译为:
ASkullIsaw;
myownheadcametomind.同上。
Iumnwind
Igraspmyrapier
Withsurgingtear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4页。
I,whowearascholar’scap,
suddenly,arrivedatfiftyyears,
impatientlyasoldier’scloak
andbreechesdon.《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3页。
从译文可见,扬女士真是用了心。可惜她的汉学功力有限,连诗题都译错了。事实上,诗题中的“虏”就是诗中的“索虏”。南北朝时,北朝人有辫发,南人对北人蔑称“索虏”。陆游诗中的“索虏”,意指屡犯宋境的金人,是对异族宿敌的一种贬称。扬女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所以才会望文生义地把诗题中的“虏”译为“战俘”(thePrisonersofWar),诗题的意思也就成了“听闻战俘骚乱”,而不是“听闻金廷内乱”。这两件事看来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一字之差,改造了整首诗的内涵与基调。
钱锺书调侃“头颅自揣已可知”的译文说,现实的情形哪有这么恐怖?陆游所谓头颅,不过是指头皮毛发,而不是指头骨,全句的意思是说,抚摸满头白发,感受到自己的苍老,而不是扬女士理解的那样,诗人因为看到一个头骨,想到了自己的脑袋。《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3页。对于第二则译文,钱锺书幽默地指出,这是让女人的武器——泪水,玷污了男人的脸颊(Thisissurelylettingwomen’sons,water-drops,stainhisman’scheek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4页。他紧接着指出,以“graspmyrapier”翻译“抚剑”一词,不够准确,因为“抚”这个词的意思是抚摸或触摸,“grasp”意为抓住、抓紧,更能凸现男性的力量。同上。其实,“抚剑”也有“按剑”的意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抚摸”,凯德琳·扬的译文似可备为一说,不必一棍子打死。
钱锺书介绍《闻虏乱有感》一诗的背景说,当时盛传女真族(theJurs)内乱,面对收复故土的良机,年近五十的诗人虽然血气已衰,却依然热情高涨,可是,“唉,就像力士参孙”(alas!likeSamson)《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4页。,此时的诗人,思绪万千,难以自已——“时光流逝,我曾是谁,如今又是谁?”同上。凯德琳·扬没能传达这种情绪,因为她没有读懂陆游的沧桑之感。
在为凯德琳·扬的英译陆游诗选所作的序言中,桃乐丝表情夸张、语调亢奋地渲染了陆游诗的爱国热情、尚武精神在中国抗战时期的巨大影响:“由于陆游所处时代与现代中国颇为相似,当今的爱国青年因此常常吟诵着陆游那些激动人心的诗句。……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纷纷诵读、引用陆游的诗歌,狂热地崇拜他,其影响力超过了任何其他作家。”《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4—335页。钱锺书调侃说,这是典型的文学推销员口吻,如果信以为真,就会陷入真假莫辨的窘境(Totakeitseriouslyisnottoknowhowtobeseriou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5页。
客观而言,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形象确实非常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诗作中确实包含着大量奔涌着为国从戎的热忱与收复故地的梦想的篇什与佳作,另一方面是因为南宋以来历朝士人、诗家的大力揄扬。中国知识分子向有报国安邦、兼济天下的理想,在基于陆游的爱国尚武诗篇及其从军生涯而衍生的想象中,这种理想似乎成了触手可感的现实与激情涌动的生命气息,因此,陆游就成了一个可以让后世爱国诗人、热血男儿投射自身激情与抱负的巨大符号。钱锺书介绍说,“约20年前(也就是1926年前后——笔者按),一位中国女作家写了一部激情昂扬但有失片面的评述陆游之作,题为‘爱国诗人陆游’。文学史中的粗浅错误很难根绝;抗日战争又为错误的延续提供了契机。一些大学里的中国文学教授发现,描写爱国志士是一条抒发爱国热情的好路子,陆游的诗于是成了他们写作时的主题或触媒。如今,一个遥远的域外独唱者的声音加入了这个大合唱。……在陆游所处的时代,复仇主题常见于作家笔下,正如在色当战役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对复仇这个话题也是念兹在兹”《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7页。。早在1899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翌年,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写下了《读陆放翁集》一诗,在这首诗中,陆游作为集剑气、诗心于一身,融诗魂、国魂于一体的爱国诗人的符号效应放大到了极致,诗云: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梁启超:《读陆放翁集》,《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下)》,中华书局,1936,第4页。
事实上,在陆游流传于世的九千余首诗中,表现“从军乐”的诗作还不够半数,其余的大量诗篇表现了多种情感意向,比较突出的有农家乐,如“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游山西村》)、“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小园》)、“高柳簇桥初转马,数家临水自成村。茂林风送幽禽语,坏壁苔侵醉墨痕”(《西村》);怀旧情,如“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客中愁,如“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剑门道中遇微雨》);也不乏文人墨客常有的伤春悲秋之感,如“山村病起帽围宽,春尽江南尚薄寒。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断香漠漠便支枕,芳草离离悔倚栏。收拾吟笺停酒碗,年来触事动忧端”(《病起》)等。陆游的异代知音梁启超所谓“集中什九从军乐”固然是夸大之词,其异国“粉丝”凯德琳·扬、桃乐丝“不爱红装爱武装”,热衷于渲染陆游的尚武精神,也难免片面之嫌。诚如钱锺书所言,“成为一个爱国者是一回事,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是另一回事”(Butitisohingtobeapatriot,andquiteaobeapoetofpatriotis)《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47页。。也就是说,身为爱国者的诗人,不一定仅以爱国主义为创作主题。
钱锺书还特别指出,凯德琳·扬的最大问题在于,她“只看到了陆游作为爱国诗人的单一形象,而忽视了他在作品中所显示出的人性弱点”(MrsYoung’sLuYouiseveryatomthepatriot-poetandhasnosuchhumanweaknessinhisposition.)《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5页。。这种从主观需要出发突出某位诗人单方面特质的思路与操作方式,往往会将复杂多元的诗人形象简化、锐化为象征某一类精神的显赫符号,陆游形象在后世塑造乃至域外传播中的际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二罗马三神与陆游诗的分类问题
尽管如钱锺书所言,凯德琳·扬过于突出了陆游的爱国诗人形象,但从凯德琳·扬对陆游诗的分类来看,她也并非对陆游形象与陆游创作倾向的其他一些侧面毫无所知。按照钱锺书本人的介绍,凯德琳·扬将她所译的陆游诗作以“爱国主义”(patriotism)、“自然”(nature)和“旅行”(travel)为主题分为三类。《批评札记三》,《钱锺书英文文集》,第338页。但她错将《书愤》一诗置于“旅行”诗之列,又莫名其妙地(forsomeinexplicablereason)将《睡觉闻儿子读书》一诗看作题咏“自然”之作。事实上,《书愤》应属“爱国主义”诗篇,而且泛览陆游诗作就会发现,他的众多爱国诗篇都被冠以“书愤”之名。同上。陆游“好誉儿,好说梦”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三七则“放翁二痴事二官腔”,中华书局,1984,第132页。,“好谈心性之学”同上。,《睡觉闻儿子读书》一诗可以说兼而有之:
梦回闻汝读书声,如听箫韶奏九成。
且要沉酣向文史,未须辛苦慕功名。
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
老病自怜难预此,夜窗常负短灯檠。陆游:《睡觉闻儿子读书》,《剑南诗稿校注》,第1818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都市风流仙医丹青
- 干涸地火风L
-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
- 假如你重生到高考前(浴火重生,绯色无疆)【清水】佚
- 薛凝封羡失去七情六欲快死了,全京城为我哭坟薛凝封羡后续+完结
- 开学第一天就被姐姐调教成狗(sm,1v1,校园h)黎戚
- 被亲弟弟内射九十九次芙蓉夜雨
- 催眠调教app昨夜骤雨打窗
- 糜烂病(gl骨)醍醐灌顶
- 娱乐:巨星演员一条舔狗
- 软香(1v1)h苏玛丽
- 催眠美母怀孕吞精精液进化丝袜足佚
- 极品家丁同人之昔游记大春袋系我
- 玩具(一部纯粹的sm向作品)伯未有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高贵强大的金发公主,才不会被潜伏进来的区区邪教徒,催眠调教后堕落成人格排泄雌媚牝妻呢!风羽飘零
- 赵浅悠宋念舟他叫我不要回头
- 黄历师石头羊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在三无冰龙娘的诱惑战下逐渐染上败北射精癖的冒险者听雨
- 穿越到遍地爆乳肥臀痴女的世界KFC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叉
- 催眠后爆奸家人佚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
- 欲火(出轨,1V1)碎碎平安
- 两小无猜(校园1v1,高H)鲸落
- 催眠后爆奸家人佚
- 《失语者的情歌》俞笙禾黎知宇《失语者的情歌》俞笙禾黎知宇
- 西游艳记老糊涂
- 原神 可以色色!瞳
- 二次元催眠调教日记月
- 催眠之御姐熟妇让我操(控制)华
- 妈,您人设崩了!臀控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南有嘉鱼(父女)鬼鬼
- 超级淫乱系统a
- 亲爱的小孩(母子h)一条孤狼
- 方永的性奴警花妈妈和母狗班主任一
- 开学第一天就被姐姐调教成狗(sm,1v1,校园h)黎戚
- 第一男後任飞
- 我有九千万亿舔狗金(系统帮我睡女人/系统帮我开后宫)番茄第一帅哥
- 尸妻美人尸妻美人
- 高冷的丝袜女总裁妈妈被混混同学屈辱玩弄h
- 朱唇轻启吻芳华小观音
- 为了治疗丈夫的勃起障碍,只好和儿子上床的教师美母大龙猫dalongmao
- 共犯(父女)roro
- 优雅迷人的金发大小姐奥黛丽和冷艳无口的木偶小姐莎伦被壮汉破处奸淫,最后双双恶堕为淫纹性奴凝夜紫
- 让你去补课,你和校花家教好上了?老陈爱喝酒
- 捡到邻居手机后(高h,1v1)规胥
- 催眠美母怀孕吞精精液进化丝袜足佚
- 攻略反派小意思,系统才是真该死云梦也
- 朕的后宫系统上线了(女尊)夏宜修
- 好眠雨季童知意
- 民国恶女求生游戏苟分日常鲸鱼糕
- 说好的炮灰前妻你怎么飞升成神了林三枝
- 在惊悚副本养师父的那些年十颗米
- 厂里那个娘娘腔昨夜听雨
- 转生成小蘑菇了长生千叶
- 当老实人扮演渣攻后[快穿]甜到萌芽
- 身穿后大师姐为我堕魔了持舒盛
- 讲书先生的新书仙缘记讲书先生
- 糟糕!气运之子是疯批(快穿)谩行舟
- 崽崽携娘改嫁,靠着众爹躺赢了红油干拌饺子
- [足球]爱吃麻辣生存指南绝世嬷童降临此世
- 人,你可以倚靠鸟的胸膛星愉
- 主角对你极度痴迷香甜小苹果
- 小马:我读书少别我,这是友谊?茶楼里的小书生
- 年代文里的街溜子采榆
- 回到七零嫁糙汉周鸢
- 大乾风华录提左司
- 我在贝克街绑定伦敦城市意识白沙塘
- 和死对头互穿后乌合之宴
- 沧浪台崎怪
- 表姑娘撩错人后一砾沙
- 权臣火葬场实录乌合之宴
- 被敌国雌虫上将反攻了花落泥
- 权臣火葬场实录乌合之宴
- 转生成小蘑菇了长生千叶
- 论挽回月下救世者的可能性帷幕灯火
- 表姑娘撩错人后一砾沙
- 回到七零嫁糙汉周鸢
- 装瞎小白花,但万人迷南园赤松
- [综英美]莫比乌斯之环维摩
- 把暗恋对象捡回家后风月无主
- 好眠雨季童知意
- 牛郎织女但女尊[gb]沈流光
- 沧浪台崎怪
- 给大唐皇帝直播种田的日常宋不破
- 身穿后大师姐为我堕魔了持舒盛
- 恋爱脑小夫郎重生了五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