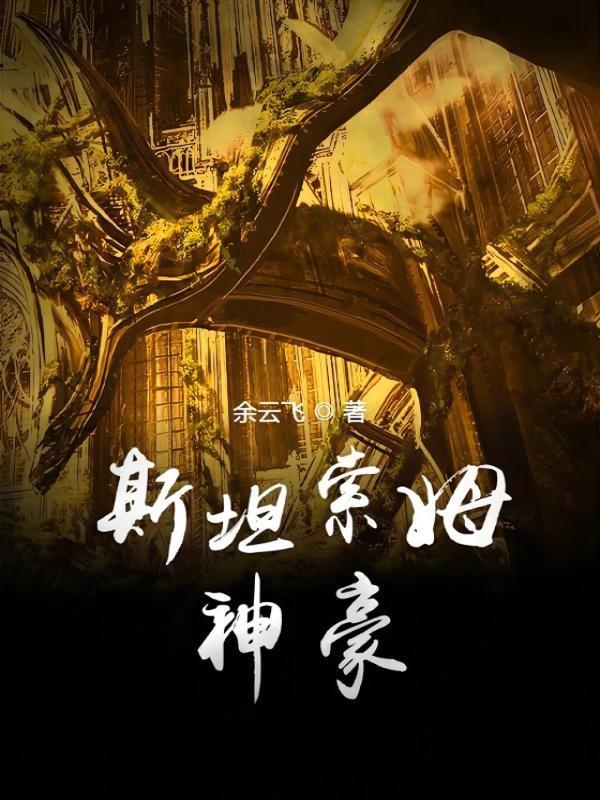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4(第1页)
4
十二月十七日,论公历已是1897年1月19日,但还算丙申年。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一切腐烂的东西都烂到了极限,仿佛悬挂于树梢的那些风干的果子,微风一吹便会跌落尘埃,而一切新生的事物,则在积雪烂泥的掩埋下,悄悄钻出坚硬的冻土。想想这一年所经行的北京、上海、南京、武昌等地,谭嗣同觉得自己真像天空中被风雷催动的一朵云,飘来荡去,莫知西东。人还刚过而立之年,他却已深尝浮生之哀乐。旧年已所剩无几,明天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他虽然抱有新气象的希望,但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会将一个人吞没。
如果说空间的转换,在无形之中塑造了时间,那么身居其中的每个人,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谭嗣同到南京后,抓紧处理完一些杂事后,就投入了撰写《仁学》的紧张工作之中。他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已得数十篇矣,少迟当寄上”。早在上年八月吴雁舟来南京代表梁启超约稿后,谭嗣同就开始构思并撰写,中间虽有办矿等其他事务耽搁,但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撰写。
在撰写过程中,谭嗣同曾将一部分书稿拿给梁启超看过,并征求对方的意见。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迭相商榷。”谭嗣同多年来遍读古今典籍,却又苦于找不到方向。就像是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从一个路口到另一个路口,看着都像是能够走出去,可是太多的岔路让他不知到底该选择哪一条路。有些岔路走下去,就成了找不到出口的死胡同。他的好友宋恕看了《仁学》,又拿给浙江余杭的维新人士章炳麟看,章“怪其杂糅”。这确实道出了《仁学》短板所在。
①哲学思想
谭嗣同重视“仁”这一观念,康有为则认为是受了他的影响,梁启超也在《仁学·序》中作此看法。实际上,谭嗣同仁学思想的主要来源仍是张载和王夫之的思想。谭嗣同在二十五岁以后,受张载和王夫之这一思想传承的影响极深。至于康有为,不过是起到一个助缘的作用。张载的《正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他本着儒家的入世精神,强调宇宙不是虚无,而是实有。张载受《易经》的影响很深,他认为气中蕴含着相荡相感的阴阳二性,因此气不会停止在太虚的状态中,而是“升降飞扬,非尝止息”。他的宇宙观是动态而非静止的,不过这种动态并不妨碍宇宙之和谐。
王夫之虽自认是张载的思想传人,但他的思想有其独立性和复杂性。张载本着“实有生动”的观念去发展其气一元论,王夫之则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挥儒家的入世精神。他批判宋儒的理气二元论,认为理是气的属性,气在理也在,理与气是不能分开的。谭嗣同在三十岁以前所写的札记中,已有承袭张载和王夫之所阐扬的“气一元论”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仁学》里仍然支配着他的宇宙观。
谭嗣同撰写《仁学》时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庞杂,除了张载、王夫之的气一元论,其中还包含为今文经学家所推崇的儒家经典、老庄著作和墨子,以及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他在《仁学》中还引用了一些自然科学和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同时也吸收了佛教的轮回和性海之说、基督教灵魂不死之说。这些“思想资料”在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上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矛盾,但谭嗣同都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渊源,这就难免会陷入矛盾与混乱。
《仁学》作为一本哲学文本,是相当枝蔓芜杂的。有些东西于他而言,也是糊里糊涂的,因为和传统的知识结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谭嗣同抓住了信仰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以心挽劫”,弄佛学,弄西学。在西学当中,他想把这些东西化解,最后搅成一锅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本质主义。老认为有一个东西是一点就破,全盘皆赢。谭嗣同的心路历程在其中都有体现,一种是日趋强烈的宗教心灵,另一种是他因受多方的影响而思想领域逐渐开阔,再一种是他对文化和政治的态度日趋激烈。谭嗣同的看法和想法,虽然有些地方失之片面,甚至是幼稚的、天真的,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个“仁”。他认为这个价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是所有道德观念的总汇。
谭嗣同把原来继承张载、王夫之的物质性的“气”用了一个叫“以太”的科学概念,其希腊文的原意是燃烧、点火,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设想出来的一种媒介。谭嗣同找到这个假设的物理学名词后,感到无比的高兴。因为在他看来,用朴素的气一元论来说明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和精神现象还很牵强。他指出:宇宙间充满着“以太”,大到地球、太阳系和银河系以至其他更远的天体,小到一片树叶、一粒尘和一滴水,它们都是“以太”凝结而成,并使之同其他事物相联系。谭嗣同不仅认定“以太”具有“不生不灭”的性质,而且由于他相信“以太”具有能使各种事物“互相吸引不散去”的功能,就断定“以太”具有“知”的属性。就是金石、砂砾、水土等,它们既能在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相互作用,也就不能说“无知”。就像他认同佛教教义,其中包含着的许多善意的成分,即使对于那些不相信的人,也是有意义的。就这样,“仁”就伴随着“以太”而成为《仁学》中的重要范畴。
谭嗣同经常会走出困顿身心的公馆,漫无目的地走到大自然里,或是寺院中小憩身心。这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也与他此时的心态有关。他看见天空明朗、阳光普照,大地如同洗濯后那样洁净,飞禽走兽悠然自得,草木欣欣向荣。而这一切在谭嗣同看来,也是“仁”的一种体现,是由“以太”的“动”而促成。谭嗣同根据《周易》强调“动”和“变易”的观念,并结合西方传来的进化论,认为客观世界的事物由于运动变化,才不断向前发展。他相信生物进化,相信它们能够从低级到高级,越到后来越超过前人,并由此发展为“日新”学说。他认为天地、日月、草木以至人的血气,都因能够“日新”才不丧失它们各自具有的特点。也正是因为他重视事物的运动变化,所以提倡“破对待”。所谓“破对待”,也就是破除事物的矛盾。谭嗣同主张运用“格致”即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来“破对待”。在他看来,事物的运动,并不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而是瞬息万变、根本不存在相对的静止状态。他说:“旋生旋灭,即生即灭。”由此,谭嗣同论断,对于“大小”“多少”“长短”“久暂”等“对待”,也按照这一说法去理解。
禅宗认为人要活出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取决于你所达到的境界。人的境界决定于“小我”与“大我”的分界。“小我”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大我”则是把小我放大到与时间、空间等量齐观,小我融于宇宙之中而与宇宙合一。在这种境界中,与“小我”有关的一切都全部消失,人从“小我”的烦恼中得到解脱。仁在谭嗣同的思想里不仅代表一种道德观,更代表一种宇宙观。正如他在强调仁为诸德之冠时所说:“天地亦仁而已矣。”
谭嗣同在《仁学》里抛开那一代知识分子所谓儒家正统,深度地去探究生命问题,宇宙观、人生观的问题。在佛学方面,按照当时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最感兴趣的是华严思想。这出自《华严经》——佛教里一部经典著作。《华严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佛学思想,就是对待生死的根本看法。它说人的生命其实就像宇宙中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它是不灭的。而我们形体的这一生,只是一个能量的暂时的显现,你到下一世可能以另外一种能量显现。
在钻研佛学的过程中,谭嗣同把佛学宣传的“一多相容”和“三世一时”的观点奉为“真理”。这两个观点都是华严宗的法藏提出的命题,“一多相容”是说事物的本体和现象能够互相包容,而“三世一时”的意思是,任何事物的生灭非常快,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体现了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程。佛教上讲到对生死问题的彻底看法,其实需要一定的实践性,也就是我们讲的修行。佛教里对生死的看法,一类是靠智慧,一类是靠意志力,而这让谭嗣同的信仰成为他的力量。谭嗣同这个人意志力很强。他用意志力来说服自己,生命其实是不会断灭的,是不断循环往复的。
在《仁学》中,谭嗣同还着力阐述了他的认识论。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使认识论和自然观保持一致,反倒由于采用不同的“思想资料”,而使二者处于分离的状态。他论述自然观,主要是依靠他所掌握的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根据,所以表现出了相当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而在阐发他的认识论时,却把自然科学知识丢在一边,完全以佛教法相宗(唯识宗)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是一种唯心学说。在他的自然观里,“以太”被规定为万物的本源和媒介,是物质性的东西;“仁”则是由“以太”把各种事物贯通为一体而形成的绝对平等、同一的状态,它是一种精神现象。但在认识论里,他用“心力”代替了“以太”,将“以太”能传播光和电,能递送信息的功能寄寓于“心力”之中,认为“心力”也能“感人使与我同念”,通过“心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②批判思想
谭嗣同在仁的观念里融摄了儒家以外的许多思想,也由此产生一种激进的抗议精神。他认为,“名教”的“名”是统治者主观创造的,并无事实依据,意在“钳制天下”,即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从而束缚他们的行为。在人世间到处都是名的笼罩和桎梏。名似乎在人世间布下了天罗地网,因此要完满地体现“仁”,就要做到“冲决罗网”。封建统治者公开要求被统治者遵循其所制定的“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并且通过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和政令等方式,大力宣扬这些道德规范,造成一种笼罩于整个社会的浓烈气氛,使被统治者的心理陷于麻木甚至蒙昧的状态。
这种抗议精神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仁黜礼的思想。就仁而言,谭嗣同认为礼是一种障碍,只有把这种障碍除去,仁才能完全实现。他在《仁学》里展开对礼的全面批判,而这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礼的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思想,其中攻击最烈的是“君臣一伦”。他觉得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壅塞和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法充分地交流,心灵无法沟通。谭嗣同认为,君主制度是造成壅塞和隔阂的一大原因,而君主制度的根源就是人的私心。所以从仁恶立场来看,君主制度不但违背了仁所蕴含的平等精神,而且也违背了仁所代表的“通”和“公”的思想。从此出发,他在《仁学》里痛斥“君统”,指出两千年来“君统”在中国造成了“大盗”与“乡愿”并存的世界。诚如他所言“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由是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大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
谭嗣同在《仁学》里不但否定了传统的“君臣一论”和两千年来的“君统”,还提出了新的“君主”观念。他认为“忠”实际表示“中心”,即待人接物一律均等、“心”无偏袒,是人与人之间双方都应有的道德,如果把它解释为臣民单方面在道义上对君主应尽的责任,那是不符合“忠”的本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也无暇相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君主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不是君择民,而是民择君。
谭嗣同对汉朝以来的各个朝代提倡“尊君统”和“忠君”的儒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攻击。例如唐朝的韩愈在《原道》里宣扬君主生下来就是发号施令的,臣僚辅佐君主统治人民,人民则必须老老实实地从事生产和贸易来供养统治者。谭嗣同认为韩愈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谄媚君主,把人民视为“犬马土芥”。到了宋朝,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更变本加厉地鼓吹君权至上,得到君主的特别赏识。几百年过去,时至今日,许多守旧的官僚、士大夫,他们仍抬出程朱理学作为反对变革的理论根据。
谭嗣同不但批判“君为臣纲”,而且对“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也提出批判。他宣称父子平等,“父权”是不合理的存在,而“孝”更不应该成为富有政治性的不可触犯的道德规范。至于“夫为妻纲”,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体现。他认为“重男轻女”是最“暴乱无理”的表现。他指出,传统社会的性关系是以女人为牺牲的。有钱有势的男子,娶妻后又讨小老婆,终日纵情于淫欲之中,毫无顾忌。而妇女偶然失身,却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罪责,往往将其杀害或逼其自尽。他尤其痛恨那些将女婴溺死之人,咒骂他们比豺狼虎豹还要凶残。他同情妇女在封建包办婚姻中遭受的困难,而不能自己选择配偶。她们的丈夫“自命为纲”,对她们不尊重,甚至给予非人的待遇。虽然她们不堪与丈夫共同生活下去,但仍不能“下堂求去”,没有要求离婚的权利;有的丈夫已死,也不能改嫁,只有忍受种种痛苦,默默地忧郁地断送自己的一生。谭嗣同在描述妇女的不幸遭遇时,洒下同情的泪水,发出愤怒的呼号。他不但要求人性的解放,而且要求男女两性的平等。
谭嗣同主张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打破,而归之于平等的“朋友”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人与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对立和隔阂得以清除。他认为朋友之伦应该取代三纲而为五伦之中心,人际关系应该以朋友关系而非三纲为圭臬。
③变革思想
谭嗣同喜欢阅读古人留下的兵书战策。有人将其视为男人征战杀伐的秘诀,可是在他看来,瞬息万变的战场如同一个国家的命运有着各种变化的可能。谭嗣同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夫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川上逝者之叹,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人生活在这天人一体的宇宙中,并不是一片静寂,而是一个生生不息、充满着活跃变动的过程,而且这个变动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变动,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变动。
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些环绕“变动”观念而展开的传统思想,在《仁学》中已质变为一种歌颂动力的勘世精神。他赞美西方充满动力的机械文明和工商社会,特别指出“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他对中国传统社会深表责难,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处事做人以柔静为主,而柔静代表一种生命萎缩的态度,与仁所代表的“生生不息”的态度大相径庭。此外,他在“柔静”之外,特别提出传统所谓“俭”德来批判。每个人都知道柔静是道家的态度,而“俭”在传统社会里却是人人都尊重的美德,可是在“俭”德之后却隐藏着一种与柔静相似,代表着保守、消极、怯懦、萎缩的心态,他说:“中国守此不变,不数十年,其醇其庞,其廉其俭,将有食槁壤,饮黄泉,人皆饿殍,而人类灭亡之一日。”
谭嗣同针对“柔静”而提出“动”的观念,针对“俭”而肯定“奢”的观念。所谓“奢”,即工商社会注重开源以使世界变得日益丰盈富有的心态。对于谭嗣同而言,“仁”代表自然人性的解放、生命的发扬、宇宙的繁荣滋长。从这些观念出发,他批判了传统社会。
谭嗣同的批判,是从批判君主专制而来。当然在19世纪末,批判君主制度已非首创之举。谭嗣同的批判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他在阐释“仁”这个理想时,特别强调“通”的观念。他觉得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壅塞与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法充分地交流,心灵无法沟通。而这一切,都是君主制度造成的。君主制度的根源就是人的私心,所谓“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所以从仁的立场来看,君主制度不但违背了仁所蕴含的平等精神,而且也违背了仁所代表的“通”和“公”的理想。从此出发,他在《仁学》里痛斥“君统”,君主以“天”之子自命,为所欲为,残民以逞,臣民若不服从,则以“叛逆”的罪名而立即杀害,并株连其亲属,实际上,君主的宝座却是真正从“叛逆”中夺取来的。君主常用“伦常”来钳制臣民,而他们才是破坏“伦常”的魁首;他们的妃嫔多得不计其数,却又不允许别人过夫妻生活,下令将宫中的男人“割势”。
谭嗣同指出,君主的宝座,原是“公位”,“人人可以居之”,如果君主“不善”,人人都可以把他杀掉。如此算不上“叛逆”,而是正义的举动。因为“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鼻四耳,而智力出于人”,所以人民不应该绝对服从他,听任他作恶而不管。他说,在远古的人类社会,本来不存在君臣关系,后来由于需要有专人管理生产和生活的事情,才由大家“共举一民为君”。民是“本”,而君是末。世上没有因“末”而累及“本”的,难道可以“因君而累及民”吗?君既由民共同推举,也就可以由民共同废弃。他所说的“君”,并不是皇帝,而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总统。因为他的语句里出现了“前有尧与舜,后有华盛顿”,他大呼“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也就是说,人们只应为国事而牺牲,决不应为君主而“死节”。
这些思想显然是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学者张灏认为,谭嗣同之接受民主思想,是透过仁所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基于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君主制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
谭嗣同对“三纲”做了彻底的攻击,当这些重重的罗网被扫除之后,他所追求的“仁”的精神——无私的爱才能“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为了体现仁的精神信念,任何外在的制度、法规、习俗、仪式甚至学说、理论都可能构成障碍,因此都要超越,都要否定。谭嗣同的言论过于激烈,因此失去生前发表的机会。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唐才常分别把所藏原稿或抄本先后发表于《清议报》和《亚东时报》,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称赞谭嗣同的《仁学》是“打破偶像”之书、“冲决罗网”之书。谭嗣同在《自序》中也层层撕开冲决的罗网:“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罗网,次冲决天之罗网,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罗网,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时至今日,捧读《仁学》虽让人有血脉偾张的快感,但其中的思想局限让人难以认同。在时间的冲刷下,昔日之新也是今日之旧,更何况彼时的谭嗣同接受新学及西学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融会贯通。不要说今日读来有过时之感,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背景下,仅仅数年之隔,亦有隔世之感。诚如梁启超后来所言:“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竭力为其开脱:“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
冬日的光阴总是那么绵长,太阳照到的地方万物是明亮的,待到山墙的另外一边天地便混沌起来。1897年,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他们像候鸟一样受一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甚至湖南的浏阳和长沙迁徙,他们的迁徙虽然并不仅仅为了寻找政治或是经济上的庇护,但迁徙造成的则是中国近代思想火种的一次次播撒,一次次蔓延。
这个冬天,谭嗣同仅仅拜访和接待了几个平日跟自己有交谊的朋友,大多时间,他都一个人躲在南京东关头公馆里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有时奋笔疾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这一日,谭嗣同在南京公寓读到《时务报》上严复写的《辟韩》时,不禁大叫“好极好极”。他读过严复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这是一个比他小一岁,与他一样经受了近代西方文化洗礼而自负的年轻人。严复在《辟韩》里,借着对唐代文人韩愈《原道》的批评表达了对民主的赞同。韩愈把圣人的形象抬高到超人的地步,而把民众描述成了一个个完全呆滞的无灵魂的肉体。在严复看来,这种对民众体力、智力和道德的严重低估和漠视,成了近代中国可悲地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谭嗣同没想到,严复的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并授意一个叫“屠仁守”的御史撰写《驳论》一篇,并以《辨〈辟韩〉书》为题,发表于《时务报》。严复在一封家书中懊恼地说,其实他已经猜测到了授意写批驳文章的人十有八九是张之洞本人。
此时求新求变之人毕竟是少数,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也是少数,人群中多的是麻木者、保守者,还处于昏昏然的状态。对于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这样醒来的人是痛苦的,他们看到现实的危险性,于是大声疾呼,奔走相告。而那些仍昏睡者显然不适应他们的做派,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搅了自己的好梦。据说,张之洞还放出话来要找严复的麻烦。严复恐罹不测,找了郑孝胥等人从中说情,方才平息此事。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玩弄暗卫的一百种方法曲书宁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玩具(一部纯粹的sm向作品)伯未有
- 穿越到遍地爆乳肥臀痴女的世界KFC
- 白给幻界之苗床女骑士绝不吃亏地熏地后
- 王博郑天乐死后第四年,被我抛弃的盲人老公终于发现我死了
- 仙子破道曲漆黑烈焰使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欲望开发系统Glasya
- 沈清然霍宴辞一夜情深霍先生宠妻无度结局+番外
- 豪乳老师刘艳t
- 公主的小娇奴(NPH,男生子)请药师赐福于我胞
- 开学第一天就被姐姐调教成狗(sm,1v1,校园h)黎戚
- 催眠后爆奸家人佚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
- 神豪的后宫日常大香蕉
- 勇者的传说女同伴们被魔族一步步肏到淫堕夜那
- 软香(1v1)h苏玛丽
- 都市风流仙医丹青
- AWM[绝地求生]漫漫何其多
- 都市奇缘易天下
- 在三无冰龙娘的诱惑战下逐渐染上败北射精癖的冒险者听雨
- 欲火(出轨,1V1)碎碎平安
- 高贵强大的金发公主,才不会被潜伏进来的区区邪教徒,催眠调教后堕落成人格排泄雌媚牝妻呢!风羽飘零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江湖孽缘(修订版)红绳紫带
- 名义:人在军阁谁敢动我孙儿同伟好溪之澜2025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我有九千万亿舔狗金(系统帮我睡女人/系统帮我开后宫)番茄第一帅哥
- 四合院:我在四合院有个青梅竹马梦想车厘子自由
- 月明星稀月明星稀
- 亲爱的小孩(母子h)一条孤狼
- 我的卡牌后宫我想躺平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仙子的修行k
- 陈斌高婉君绯色青云陈斌高婉君后续+完结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叉
- 真搞熟妇亲人呸
- 二次元催眠调教日记月
- 仕途佳人仕途佳人
- 官路美人迎风笑
- 乱伦天堂黑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女神攻略调教手册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仙母种情录欢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我和淫乱后宫们的ntrs性福生活chuya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青春砍杀俱乐部CP孙黯
- 大小 姐的航海训犬日志+番外程十予
- 看见她秦阿玉
- (综漫同人)非酋如何在柯学世界生存+番外AAA泽宣
- 女A恋爱指南[GB]+番外纸北针
- 走绿茶的路,让她无路可走+番外饭团爱上了菜包
- 在星际世界办宠物收养/和收养的流浪猫猫狗狗一起穿到星际了+番外戋离
- 被劝学的童养媳[民国]老牛夜里挑灯耕甜文
- 队长挖我千年古墓,还想和我同棺摸鱼大喜
- 惨遭流放我卷走物资带着全家跑了+番外柠桉
- 快穿:别惹她,黑锦鲤有疯是真发懒癌晚七
- 快穿:白莲花攻略日记呆头鹅啊
- [综漫] 摆烂失败五条决定大杀四方虚空无苦
- 仙二代的小道长土豆鱼儿
- 健身房教练x牙科医生秀峰
- 无处可逃(np)暴走糖炒栗
- (综漫同人)最强幼驯染卜咕鸟
- 匣中宴匣中宴
- 沉墨告白(gl H futa)卧花海
- 祝同喜啴七
- 爱欲成瘾 (短篇H合集)蓉蓉
- 穿越国外写小说姬赢
- 小潭山没有天文台CP清明谷雨
- 不过直个播,怎么都说我是万人迷/主播天然钓,榜一大哥直翘嘴云浮宿迁
- (综漫同人)五条老师拒绝BE与子归
- 快穿:白莲花攻略日记呆头鹅啊
- (综漫同人)同桌是迹部君黑糖麻花
- 别动我的棺材铺+番外睡不醒不更新
- 队长挖我千年古墓,还想和我同棺摸鱼大喜
- 恶毒假少爷,但实在美貌龙川美美
- (综漫同人)最强幼驯染卜咕鸟
- 误发暧昧短信给高冷霸总后秀峰
- 快穿:别惹她,黑锦鲤有疯是真发懒癌晚七
- 带着空间穿到残疾夫君流放前柠桉
- 大小 姐的航海训犬日志+番外程十予
- (综漫同人)五条老师拒绝BE与子归
- 总裁O的比格A驯养日记(futa&abo)Mallll
- 惨遭流放我卷走物资带着全家跑了+番外柠桉
- 蚁鸣CP蛇蝎点点
- (综漫同人)萤丸远征手札+番外山岚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