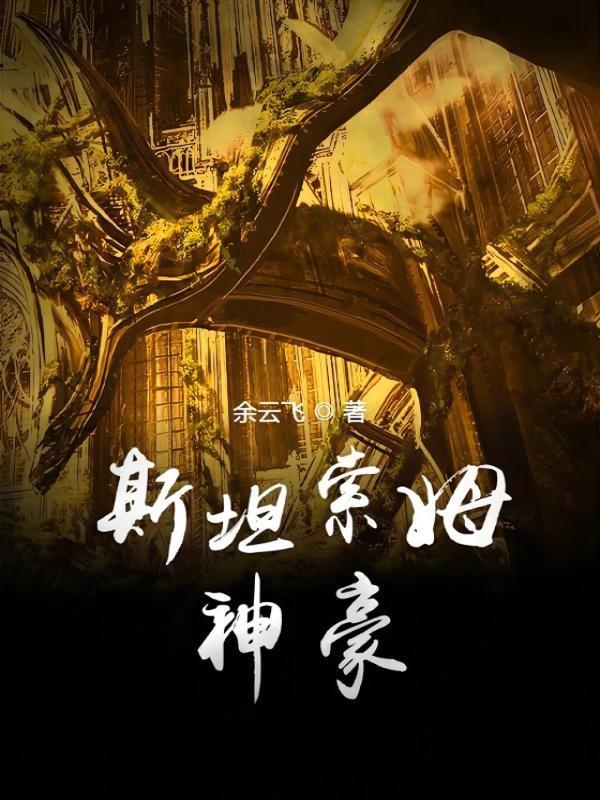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八章维新者说 湖南之士可用(第1页)
第八章维新者说:湖南之士可用
1
1897年的春节,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在南京东关头公馆度过。这里紧邻秦淮河桃叶渡码头,是一处安静所在。想起李氏与自己结婚十余年,谭嗣同不无愧疚地发现,他们就像一条河的两岸,总是聚少离多。二人婚后曾育有一麟儿,却不幸夭折。当时他们兄弟间公认,老九的老婆最漂亮,老九本人倒其貌不扬,总是要打趣老九。谭嗣同从来不参与议论,某次同族的嫂子见他在一旁不作声,便笑着调侃道:“七叔(嗣同),七婶蛮不错的吧?”谭嗣同不以为意,爽朗地回答:“是呀!是呀!配我有多,配我有多!”见他一脸坦荡,众人不由为之动容。
新年的到来和往日并无不同。除了几声爆竹在秦淮河畔的街巷里毫无感情色彩地炸响,空气里偶尔飘来肉香和祭祀的香烛气味,此外再也让人觉察不到,这是岁在丁酉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第一日。
尽管早就厌倦了开年首日里的种种繁文缛节,可是作为一个身有功名、薄有名望的体制中人,谭嗣同还是早早起了身。这是薄阴的天气,似雨非雨,天气倒也不怎么冷。行诸礼毕,百无聊赖,仍是躲进书房寻清净。南京候补一年,他很少应酬,书倒是读了不少,《仁学》也进入修订收尾阶段。在此之前,他一度感到迷茫,陷入精神困境,深感所愿皆虚,所学皆虚,心迹一日日散淡着,以至于“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或许也正是这份困惑、这份迷茫让他努力求索。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谭嗣同大致在两个方向上努力:一曰做事,二曰读书,如有其三,便是因读书而引发的思考与讨论。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诚如时人所言,天下就要亡了,国家就要亡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哪里容得下你“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到山谷中间、躲到密林深处去读书?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从完成《仁学》初稿后,谭嗣同开始认真思考推进维新运动的实际策略和步骤。
前些时日,谭嗣同写了一封信给汪康年,告诉他,自己筹划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已正式成立。而湘乡东山书院也效法浏阳算学馆,将讲习“时文制艺”改成以讲授算学为主。谭嗣同还随信附上《报章总宇宙之文说》《浏阳土产表》和《民听报式》三篇文稿。他希望汪康年能够将前两篇文稿在《时务报》上公开发表。《报章总宇宙之文说》是针对守旧文人反对报章文体而写,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文体具有充分论证宇宙间各种复杂事物及其演变道理的功用,使文章能适应时代需要。这种文体发端于《时务报》的创办,其中尤以梁启超的文字为最。梁启超的文字借助《时务报》,成为广大青年学子的最爱,也征服了一些有资历、有地位的人。后世更是将梁启超称为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执晚清舆论界的牛耳。人们把梁启超在报纸上的这种文体称为“时务体”或“新民体”,其实是现代白话文的源头,在晚清和民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人有言:“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兴趣了。”这便是新文体的魅力,即使像李鸿章、张之洞和翁同这样的高官硕儒也难以抵挡。《浏阳土产表》着眼于发展地方经济,使各种物产都能尽其用。至于《民听报式》,则是他为正在筹备创办的《民听报》所拟订的简明章程。
谭嗣同与广东维新群体的关系大为接近,同时与浙江维新群体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湘、粤、浙三者之间一直维持着平衡的关系。然而没有多久,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维新群体之间的矛盾发端于上海《时务报》。《时务报》是彼时思想家的发声阵地,是国内报纸的“报王”和“馆祖”。大量的报刊文章问世,使得梁启超、章太炎和严复等人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日趋提高。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谁能轻易发现其他人身上潜伏着一个天才思想家的禀赋。1894年那场与近代中国命运攸关的中日战争,就像是思想的天空炸响一声惊雷。国势日危的种种惊愕、忧虑和愤懑,如决堤之水倾泻而出。大受刺激的知识分子们突然觉醒,羸弱的身躯充满着无可抑制的力量,而报纸这一新兴的传媒机器将他们发出的声音放大了千万倍。
《时务报》的资金来自捐款和筹集,主要创办人为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三人。在湖南众多维新人士中,黄遵宪是唯一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人。他出使东西洋各国任外交官多年。他的《日本国志》作为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通志,“叙述了日本古往今来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明治维新’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一部‘明治维新史’”。黄遵宪先后辗转于日本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外交职位,三十八岁解任回国。他在家乡生活了五年,闭门撰写《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1890)他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四年之后,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这时,张之洞自湖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以筹备防务需要人才为理由,奏请朝廷调黄遵宪回国。
黄遵宪回到国内已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初,他的《日本国志》也于此时问世。据说有人带着这部书去见张之洞,不无遗憾地说,此书如果早些问世,可以节省二万万两白银(《马关条约》里的赔款数额)。是年八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创办上海强学会。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往南京面见张之洞。大约就在此时,黄遵宪与康有为走到了一起,他们“纵谈天下事……自是朝夕过从,无所不语”。张之洞本打算委以重任,怎料黄遵宪“自负而目中无权贵”。有人说他在拜见张之洞时,像一个不识时务的狂妄之徒,“昂首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委任他为江宁洋务局总办。他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也由此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帮新朋友,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强学会关闭后,他联络梁启超、汪康年、吴季清等人,共同创办《时务报》。黄遵宪尤其欣赏梁启超,他曾说“罗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
《时务报》一纸风行,全赖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三人之力。黄地位较高,开办时捐款最多,“报馆一切事无不与闻”。汪康年任经理,相当于今天的社长,负责经营管理,不辞劳苦,出力最多,黄、梁均承认“此馆非君不能成功”。梁启超主笔政,也就是今天的总编辑,负责报纸的内容编排,倾注了大量心血(《时务报》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时务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梁启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黄遵宪离开上海,前往北洋水师营务处赴任,报社的经济、人事、行政诸权遂由汪康年兄弟一手掌握。黄遵宪从创刊之日就不断强调,《时务报》是共同的事业,并非一家一户的买卖。他甚至还建立一套企业管理制度,“此馆章程即是法律,西人所谓立宪政体,谓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中也。章程不善,可以酌改,断不可视章程为若有若无之物”。黄遵宪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一是设董事会,由董事会统领全局。二是将立法、行政分开,有制定章程的,也有实际操作的。他甚至担心汪康年日日忙于歌舞宴请,没有时间掌管全局,于是建议让吴铁樵来上海,吴主内,汪主外。他还建议汪康年的弟弟汪诒年专门负责校勘和稽查,他也一再请求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龙泽厚来上海。
黄遵宪的一系列想法和做法,引起了汪康年兄弟的猜疑和不满。在汪康年兄弟看来,这些不过是人事替换、权力分割的借口,因此对黄遵宪大为不满,并牵扯到梁启超。于是,长期以来潜藏于《时务报》的各种矛盾也随之公开化。
随着黄遵宪的离开,梁启超与汪康年由融洽到隔阂,由分歧到矛盾,关系越来越紧张。汪康年本就是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的变法主张与改良派不同,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也始终反对。强学会在北京、上海成立之时,张之洞都捐了银子,包括后来的不缠足会、农学会等,他也都有捐赠,据说累计捐资高达五千两。《时务报》创办时,就用了上海强学会停办时剩余的银子。但他这个维新党,用严复的话说,不过是个“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时务报》既用了他的银子,他就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
汪康年在担任《时务报》经理的前期,并没有完全听从张之洞的摆布。他曾写过《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惹得张之洞很不高兴,认为他文章中宣扬“民权”思想是不对的,劝他不要依附康有为。汪康年虽心有忌惮,却没有放弃革新的思想。张之洞犹如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的一道分界线,泾渭分明,不容逾越。他经常授意亲信梁鼎芬致书汪康年,“卓如(梁启超)诋纪甚,诋倭尤甚”,并警告汪康年,“以后文字,须要小心”。汪康年还想利用梁启超扩张《时务报》声誉,也一度以“经理不能管主笔之事”相推诿。他自己也曾写过几篇讲求新政的文字,但架不住张之洞的一再敲打。张之洞是现任湖广总督,是当权的地方官僚,而那些打着改良旗帜的思想者不过是无权无势的“士子”。汪康年在言论方面变得愈加谨慎,并设法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文字加以约束,劝其不要将“康学”引入报中。
如果说张之洞是梁启超和汪康年之间的一道分界线,那么康有为则是横亘于他们之间的一道坎,同样无法逾越。康有为主张“尊孔保教”,他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甚至用了孔子纪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反对。梁启超却追随其后,大肆鼓吹。黄遵宪和严复都曾经力劝他放弃保教的主张。虽然日后他和老师发生了分歧,但彼时他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无可动摇的师尊。当汪康年、汪诒年指责他借《时务报》宣扬康有为的思想学说时,他毫不留情地驳了回去:“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康有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也就是说,天下人都知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如果说看到康有为的名字,就拒绝读《时务报》,那么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不是一样吗?
梁启超与汪康年围绕着康有为而发生的争执与争辩,一直蔓延至他们公开决裂时,直至无可回旋。梁启超曾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一文中质问汪康年:“独所不解者,穰卿(汪康年)于康先生何怨何仇,而以启超有嫌之故,迁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场中,专以诋排为事;犹以为未足,又于《时务日报》中,编造谣言,嬉笑怒骂;犹以为未足,又腾书当道,及各省大府,设法构陷之,至诬以不可听闻之言。夫谤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诬康先生之言,亦种种色色,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矣,启超固不与辩,亦不稍愤;独怪我穰卿自命维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
丙申(1886年)年底,梁启超推荐广东学人麦孟华(孺博)为《时务报》撰稿人,而汪康年也聘请浙江人章太炎(又名炳麟,字枚叔)为报馆撰稿人。章炳麟赞成维新变法,但是他不同意康有为创设孔教的主张,与梁启超、麦孟华等“论及学派,辄如冰炭”。章太炎连续发表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为人传诵一时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谭嗣同读后大加称赞,致信汪康年和梁启超:“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梁启超)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惟麦孺博先生之作尚未见,然读其《四上书记序》,亦周之南华山人也。”谭嗣同不会想到,自己无意间发自肺腑的一番话,会成为《时务报》馆内康门弟子与章太炎发生冲突的导火索。
据章太炎自述,他平时在报馆私下议论,经常将康有为比作李贽,斥之为“狂悖恣肆,造言不经”。康氏门徒向来视康有为为“南海圣人”,不容半点异议。李贽是明朝最为异类的思想家,章太炎辱及师门,自然会让康门弟子心怀怨恨。而来自江南的谭嗣同将梁启超的文章比作贾谊,将章太炎的文章比作司马相如,并未提到麦孟华,麦因嫉妒而生恨。这一日,康门弟子上门找章太炎理论,文人动起武人的拳脚。而在《时务报》撰稿人孙宝的日记里则是另一番情形:章太炎酒醉失言,称康有为为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他争辩,最后演变为全武行。
无奈之下,章太炎被迫辞去报馆职务,返回杭州,以避其锋芒。就在他离开上海的前两日,谭嗣同还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特别叮嘱代为问候“枚叔先生”。当谭嗣同在南京得知事变消息,不禁为当日言语的草率而愧疚,也为章太炎的离去而感到惋惜。他在与好友郑孝胥谈话时还心有戚然:“汪所引章枚叔与粤党麦孟华等不和,章颇诋康有为,康门人共驱章,狼狈而遁。”在这件事上,章太炎意气用事,言语不当,固有责任,但康门弟子以势压人,乃至大打出手,由此酿成晚清思想界的一桩丑闻。
谭嗣同对章炳麟抱有同情之意,他曾就此事询问梁启超:外界有传闻,《时务报》将会把浙江人赶走,而全部聘用广东人。梁启超听后大为震惊,他虽然坚持完成报纸的撰稿,但还是带着麦孟华等广东人搬出报馆,以避嫌疑。到了这个时候,《时务报》的内部之争就有了“党争”的意味。当时在上海的浙江维新人士中,宋恕等人虽有思想,但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和能力。而汪康年虽为革进派,但和康梁相比,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他不主张激烈的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容易,建设太难,尤其是中国当时面临的困境,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经不起任何折腾。浙江维新人士的这种状况,自然不能使谭嗣同满意。
谭嗣同有着急切的政治情绪,他与康、梁的激进有着天然的契合,他觉得这个老大的帝国已经病入膏肓,非得动一场大手术不可,温和的改良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嗣同与汪康年在思想和行动上逐渐产生距离,而与康、梁走得越来越近。谭嗣同也看到湖南和广东维新人士学派相同,观点接近。他不无感慨地说:“近年两省士夫,互相钦慕,接纳情亲,迥非泛泛……几有平五岭而一逵之心,混两派而并流之势。”他特别强调湖南与广东维新人士在学术上的一致性。谭嗣同最欣赏的近代湖南学者是魏源。魏源从“变”的观点出发,阐释天下万事,并且屡试不爽。魏源说过:“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变通之法。”大凡一事一物,发展既久必有弊端积累,日堆月积如不以“变”制弊,必然淹没以往所有得利之处。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羽飘零
- 我的爆乳巨臀专用肉便器王苗壮(LIQUID82)
- 糜烂病(gl骨)醍醐灌顶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季寒声沈清璇于春色暮晚相拥结局+番外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优雅迷人的金发大小姐奥黛丽和冷艳无口的木偶小姐莎伦被壮汉破处奸淫,最后双双恶堕为淫纹性奴凝夜紫
-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
- 都市奇缘易天下
- 直播也能挽救用品店吗啊若
- 无限之生化崛起三年又三年
- 高贵美艳的丝袜舞蹈老师妈妈(无绿改)江
- 在三无冰龙娘的诱惑战下逐渐染上败北射精癖的冒险者听雨
- 将警花妈妈调教成丝袜孕奴佚
-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为了治疗丈夫的勃起障碍,只好和儿子上床的教师美母大龙猫dalongmao
- 黄历师石头羊
- 【黯的旅程】魔枪舞姬的初体验逛大臣
- 软香(1v1)h苏玛丽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甜秘密(校园高H)翼山明
- Kiss Me if You CanZIG
- 大奉打更人之佛陀的阴谋对酒当歌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江湖孽缘(修订版)红绳紫带
- 名义:人在军阁谁敢动我孙儿同伟好溪之澜2025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我有九千万亿舔狗金(系统帮我睡女人/系统帮我开后宫)番茄第一帅哥
- 四合院:我在四合院有个青梅竹马梦想车厘子自由
- 月明星稀月明星稀
- 亲爱的小孩(母子h)一条孤狼
- 我的卡牌后宫我想躺平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仙子的修行k
- 陈斌高婉君绯色青云陈斌高婉君后续+完结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叉
- 真搞熟妇亲人呸
- 二次元催眠调教日记月
- 仕途佳人仕途佳人
- 官路美人迎风笑
- 乱伦天堂黑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女神攻略调教手册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仙母种情录欢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我和淫乱后宫们的ntrs性福生活chuya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北境之王:穿越后被战神娇宠了+番外看风也听雨
- 裴总捡回来的小可怜,又疯又粘人酒酒子琪
- 快穿之打倒重生文女主露娜斯朵芮
- 谁家小鱼快来认领+番外云边鹤
- 仙子破道曲漆黑烈焰使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综漫同人)拜托你了,银时老师水云烟霞
- 上错暗恋对象的迈巴赫/只有烟花知道八月糯米糍
- 故旧新逢观然
- 头七见魂CPwinter酱的脑汁
- 婚内暗恋[先婚后爱]黎纯
- 鼎炉秘典:道途淫靡长生欲道
- 秋天不回来-我的教师美母江风夜话
- (综漫同人)完美反派就业中[综]天涯晨曦
- Re:从零开始的基沃托斯恶堕计划Arch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黑莲花今天也在碰瓷我薛不会
- (古典名著同人)孙悟空三打奥林匹斯山沈镜渊
- 我的学氓魅魔女友kkkf
- 快穿之差点被带偏了+番外爱吃花生酱烧饼的犰弘
- 男子高中生不会梦到阴阳双胞胎姐妹一盘没有梦想的鱼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梦中攻略室友她哥后,意外掉马宁昏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灵能同人)穿到老公少年时+番外流浪板栗
- 替身罢了,重逢为何不放手无极烟火
- 爱过,但我选权力枕上灯
- (天国大魔境同人)命运引领我走向你+番外流浪板栗
- 重演CP放野燈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白首与君同时间在看
- 死遁后我成了仙门白月光纯情母猪
- (少女漫同人)我的男友是邪脑科学家兔子饼干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