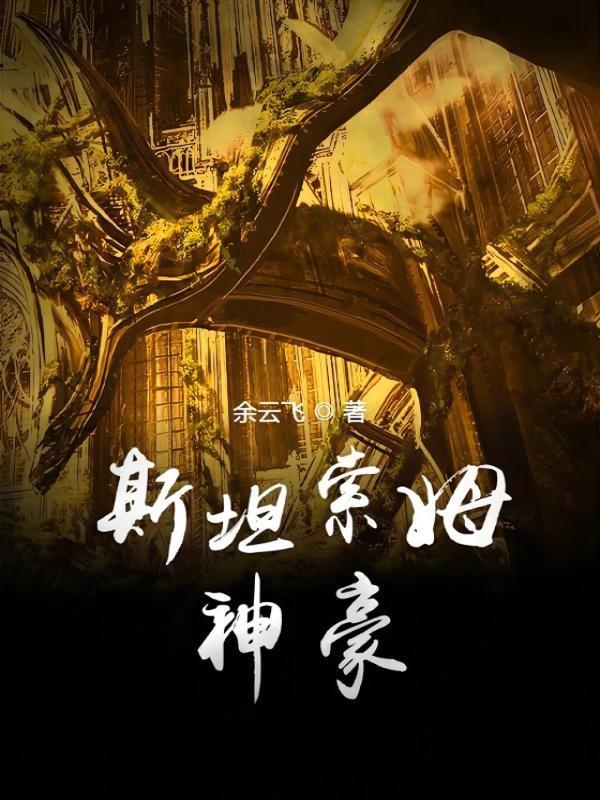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4(第1页)
4
光绪九年(1883)三月,谭嗣同赴湖北完婚。时令尚春,鸟声和花叶有着恰如其分的轻灵。妻子李闰,是谭继洵友人李寿蓉的长女。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双方都是书香世家。谭嗣同的岳父李寿蓉,字篁仙,湖南长沙人。传统婚姻守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于重门第而忽视感情,并没有为他们婚前互相了解创造条件,因此夫妻感情要靠在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去培养。
戏本里有英雄配美人,而圣贤只在纸面上谈爱情,现实里也只是将三从四德的紧箍咒留给爱情。有趣的英雄,无趣的圣贤。后者喋喋不休,像是无所不能的老江湖。而对于爱情,他们甚至比不上世间任何一个情种,他们谈的不是实在具体的爱情,而是阴阳男女化合之道,是别人的爱情,别人的体验,别人的江湖。
对于这段包办婚姻,颇富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谭嗣同起初并不满意。面对李闰这位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他曾一度产生过逆反的情绪。李闰并不符合谭嗣同心目中对于妻子的想象,过于普通。眼前这个看上去端庄贤淑、面目和善的女子,在人群中并不惹眼。个子不高,且有些富态,脸上还长有雀斑,更不懂得装扮自己。途经陕西蓝田的古蓝桥时,想到传说中裴航与云英自由恋爱的故事,谭嗣同还曾写诗自嘲:湘西云树接秦西,次弟名山入马蹄。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对于读书人来说,所谓爱情,不过是通过追求女子,将她们的德行与自己的人生目标合二为一。既要颜如玉,又要黄金屋,前者是猎色,后者是猎名利。这世上的优秀女人,可以激发男人的豪情壮志,也可以平息男人心头不切实际的狂想。她们就像是冥冥中提溜男人头发,帮助其平地飞升的神秘力量。她们把男人的灵魂提升到距离俗尘很远的地方,也可以把手松开,让他们跌落尘埃。
婚庆是人间欢喜事,大欢喜。男女情爱,阴阳之爱,乾坤之爱。就像那戏文里唱的: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这样的戏文,听上去耳熟眼热,却让人觉得不够诚恳,像少年人的心事。欢乐趣,离别苦,数十寒暑,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跨越。谭嗣同与李闰的婚姻,遵从的是父亲之命,他甚至觉得自己是这场婚姻的牺牲者。不是感情成全了他们的婚姻,而是来自两个家庭的权力叠加,是当时最流行的婚姻构建方式。在谭嗣同看来,传统男权文化哺育出来的婚姻是畸形的。它粗暴地将道德的重量,压在女人那副柔嫩的双肩上,让她们负载难以承受的厄运,借以匡扶男权秩序的脊梁。如此情态,在《聊斋志异》中俯拾皆是,那些自荐枕席、出钱置地、红袖添香、担水洒院、委曲求全的狐媚女子,她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充当救世主,一边要满足那些现实世界里四处碰壁的小男人的形而下之欲,一边要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探照灯。
这是道貌岸然者的情欲做派,在他眼里,他的父亲谭继洵即如此。谭嗣同不同,他将情义看得重于情欲。或许是因为母亲早逝带来的伤痛,让他同情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谭嗣同的岳父李寿蓉也非寻常文人,有人将他与曾国藩、王闿运等六人列为湖南六大对联大师。此人进士出身,户部任职时,颇受时任户部尚书肃顺赏识与器重。咸丰九年(1859),肃顺严治亏空,屡兴大狱,李寿蓉因库银短缺,被追究责任,入狱三年。李寿蓉生性恬淡,但命运坎坷,原配熊氏二十五岁就去世,未留下一儿半女。李寿蓉身陷冤狱时,继配夫人蒋氏正身怀六甲,听说丈夫下狱,忧急相交,两天后就血崩而亡,留下一幼女。李寿蓉出狱后,续娶王氏,接连生下三个女儿,长女即李闰。在李闰六岁那年,王氏又去世。所幸保姆高氏受王夫人临终所托,尽心抚养李闰三姐妹,视同己出,令她们学习诗文和礼节,教导其贤淑女子的种种规矩。后来姐妹皆以贤闻名,高氏离世时,李闰为其写下题照诗,云:“髫龄失母实堪怜,朝夕相依十六年。问暖嘘寒勤抚恤,追随不异在娘前。”
谭继洵很早即与李寿蓉约为婚姻,聘其长女李闰为媳。李闰于同治十年(1871)四月二十日生于北京,字韵卿。李寿蓉复官户部时,谭继洵亦任职户部。两人既为同乡,又为同僚。同僚兼同乡,这真是儿女婚姻的最好模板。李闰与谭嗣同都出生于北京,又都幼年丧母,有着相似的早年经历。当时李家寓所“距琉璃厂才数百步”,与谭家所住北半截胡同相去不远。
此后不久,李寿蓉捐资道员,分发湖北,以道员在湖北候补,携全家迁居至武昌。光绪九年(1883)三月,谭继洵从甘肃巩秦阶道升任甘肃按察使,经与李寿蓉相商,定下良辰吉日,为谭嗣同与李闰完婚。于是,谭嗣同奉父命奔赴千里外的武昌。李闰,一个知性的人间女子,就这样走进了谭嗣同的生命中。随着相处日久,谭嗣同愈发尊重妻子,在他看来李闰是上天赐予自己的最美好的礼物。他的这份感念,源于对岳父李寿蓉的感激。他称岳父家是“内外群从,率皆豪俊。登山临水,觞咏不绝。剑客奇才,献技在门。一童工书,一仆善棋,府史吏卒,傲脱不俗。所谓卖菜佣皆有六朝烟水气矣”。也就是说,不仅岳父才华出众,就连他们家的仆人也都身怀所长,或长于书法,或长于下棋,就连买菜的仆人也活得像魏晋南北朝的士人那样,很有文化气质。
妻子李闰生在这样的家庭,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从小知书达理,非常贤惠。所以谭嗣同觉得自己捡到了宝,婚后琴瑟和谐,也让他消解了许多人生的烦恼。谭嗣同常年奔波在外,李闰将家中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谭嗣同曾在结婚十五周年送给妻子的诗中写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除了门当户对,谭嗣同和李闰的婚姻能够幸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谭嗣同与众不同的男女观和夫妻观。谭嗣同向往的爱情,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没有爱情经历的婚姻者一样,都是他们心里虚构的爱情。那是一个红袖的世界、花的世界、颜如玉的世界。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谭嗣同有一个相对平等的世界观。
男人和女人都是天地间的精英,都可以成就大事业,两者是平等的。这种观点在那个时代令人震惊。谭嗣同主张“夫妻皆朋友”,夫妻双方没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彼时中国,像他父亲谭继洵那样有些财富和地位的男子娶妾,是最为平常之事,很多人一娶就好几房。谭嗣同认为在婚姻问题上,妇女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漠视。而造成这一切的,皆因三纲之苦。夫既自命为纲,女性则沦为从属,因而不以为耻。婚姻关系,应出之两情相悦,伉俪笃重,女家不要索取财力,男家不得以嫁箧不厚而生菲薄之意。时至今日,其中弊病仍风行于世,不时酿出人间悲剧。不由让人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婚姻又为何物?与其父不同,谭嗣同始终提倡一夫一妻的婚姻,一生未曾纳妾。
结婚之日,岳父李寿蓉亲笔书赠对联一副:“两卷道书三尺剑,半潭秋水一房山。”上联言养气,下联言定心,显得意味深长。李寿蓉很赏识谭嗣同这个女婿,认为他是一个有大情怀的青年,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岳父看姑爷,也是越看越喜欢。李寿蓉生性平和,风趣横生,这与他的亲家翁谭继洵截然不同。谭继洵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员、板着面孔的家长,他不怎么亲近儿女。而李寿蓉则不然,他从不在子女和下人面前摆架子。用今天的话说,他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平日里喜欢听人讲故事,自己也喜欢讲故事,他还会将那些故事记录下来。他很是欣赏自己的女婿,给予谭嗣同很多慰藉。每次谭嗣同去看望他,李寿蓉都非常开心,好吃好喝地招待,嘱咐家人为其铺上暖和的被子。谭嗣同也喜欢去岳父家,甚至觉得在岳父家比在自己家里还要舒心。后来李寿蓉调往安徽为官,谭嗣同还不顾路途遥远多次与妻子李闰一道去看望岳父。他后来回忆岳父对自己“恩礼绸至”,十分关照。两人虽为翁婿,但更是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自母亲徐五缘过世后,卢氏不待见他,加之不得不南来北往地奔波,谭嗣同时常陷于苦闷之中。光绪十年(1884),谭嗣同再次回到兰州,他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在谭继洵的安排下,谭嗣同与仲兄谭嗣襄都进入兰州的新疆甘肃总粮台谋职。人都需要身份,没有身份,人就容易被人群淹没,无从辨认。这世上沉默的大多数,都是身份模糊的人,生也好,死也罢,记住他们的是他们的亲友。活着的人,都想将自己的名和姓留下来,或跻身于史册,或镌刻于金石。于是,身份也就成了活人的通行证、死人的墓碑。这一年新疆建省,也就有了“甘肃新疆省”这个特殊的省名。“甘肃新疆省”并不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超级行省”,涵盖甘肃和新疆两省。最初的“甘肃新疆省”不包括新疆东部地区,甘肃即甘肃,新疆即新疆。两地因为地缘关系,难以分割,需要一定的“缓冲带”。第二年,清政府在筹建台湾省时提出:“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也就是说台湾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体,可以借鉴“甘肃新疆省”的制度和办法。
清廷设立“甘肃新疆省”,由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刘锦棠任甘肃新疆巡抚,谭钟麟任陕甘总督,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继洵与刘锦棠关系密切,结为儿女亲家。儿女的婚姻,亲上加亲,共生共荣,这也是官场中人将权力升级的手段。谭氏之女嗣嘉嫁于刘氏之子、新疆疏勒县知县刘国祉。谭氏兄弟在此间谋事约一年时间,谭嗣同回忆称:“陕甘粮台有汇兑之票,可汇银往应解陕、甘协饷之各省,毫不需费,票至,各省由藩库发兑,以代运饷,立意极为灵巧。”刘锦棠考虑到新疆“汉、回杂处,语言文字隔阂不通”,认为他们不适宜久留此处,就以向朝廷“疏荐”为诺,将他们劝往他处。事后,刘锦棠奏保嗣襄以直隶州知州用,嗣同以知州补用,先换顶戴。从此,谭嗣同就有了候补知府的头衔,知府相当于汉代的太守,故朋友之间有时也称其为“复生太守”。
一个人有了地位,别人便不再将其视为独来独往的个体。置身于大时代中的每个人,谁又能完全代表自己,权贵不可以,圣贤也不可以。人与需合而为儒。可见读书人在那个时代里,很难读出境界,读出的往往是野心和欲望。于是乎,那大写的儒便是有所求、有所为。人有所为,方可立世;人有所需,则摧眉折腰,虚弱不堪。由是,所谓儒,也就成了内心懦弱之人。
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节后,谭嗣同从兰州启程返回湖南,四月中旬到达浏阳。这一年八月,谭嗣同在长沙通过“录科”(未参加科试的生员等,须经学政考试,合格的才有资格参加乡试),继而参加乡试。清朝的乡试和会试,名义上分作三场来考。头场时文(八股文),二场经文(阐述五经内容),三场策问(提出有关经义或政事等问题,要求考生对答)。实际上,考官在评阅试卷时偏重头场(即偏重以朱熹注释的《四书》命题的八股文),二、三场试卷的字句只要无大毛病,就算“中式”。谭嗣同治学务求博通,二、三场考试当然能取得好成绩,但头场所考八股文,却由于他对此种形式上极其呆板、内容上只可转述朱熹的注释而不许作者自由发挥的文体,素来厌恶,即使为了应付考试去迎合,去揣摩,也难以写得完全符合考官的要求。于是,落榜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
谭嗣同在科举考试方面没有天赋,他的功名始终停留在监生这一资格上。就连监生,也是依托在朝为官的父亲打下的经济基础。谭继洵掏腰包,捐纳使其获得监生出身,算是为他叩开了那道仕进的窄门。在科举这条路上,谭嗣同始终没有停下奔忙的脚步,他先后六次赴南北省试,合计八万余里。如果将这个距离叠加,可以说谭嗣同为了科举整整要绕上地球一周。虽然付出如此之大,但他还是无法体验成功的喜悦。一次次铩羽而归,谭继洵对儿子屡试不中的状态很不满意。
他对谭嗣同的忠告,无非是读书求进的要领。当然他说的那些话,谭嗣同还是记住了一点。身在天地牢笼内,就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做一个自由人,更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虽然读的都是《四书》,但不同的人得到的东西也不尽相同。有人得到的只是考试的题目和制艺的材料;有人则热衷于故纸堆中的笺注校勘;还有人洁身自好,将其视作自身道德修养的门径;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古人的微言大义和先王之志。但说一千道一万,若无科举考试,还有几人会用心读那些儒家经典?
谭嗣同厌恶科举那一套,无法像父亲谭继洵那样,做个束手束脚的人,文也循规,人也蹈矩。他们的人生一眼就能望到头,既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便利,又抱怨着枷锁缚身的煎熬,每日就在这纠结中度过。临了,墓碑上刻满这一世的头衔。他承认自己在八股文写作方面缺乏天分,不合乎规范。在这方面,他受到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的影响,从内心排斥千百年来读书人所走的那条老路。当然,这样的人生选择也和他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相契合。
谭继洵对谭嗣同兄弟有着分工不同的安排,嗣同带在身边,督促学业,嗣襄则回浏阳经营家业。谭继升在世时,谭继洵在浏阳的地产由其代管,嗣襄辅佐。光绪十二年(1886年),谭继升在浏阳病卒,由其子谭嗣接替家庭地位。同时,谭嗣襄在经营田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谭嗣同记载:仲兄归乡经营家政,勤敏异常。米盐钱刀琐屑之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他却能将其处理得井然有序,人莫能欺。不到十年时间,增置田产百余亩。他为人慷慨好施,以义自任。他凡事亲力亲为,以己度人,就连烹饪洒扫之役,也亲自察看并记录下来。
谭嗣襄善于经营的能力,在家乡被人视为“奇士”,而嫉妒他的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在背地里讥议,说他不过是个败家子。就连他的堂兄谭嗣也不以为然,多次写信向叔父谭继洵告状。于是一封封从甘肃寄来的训诫书信,让谭嗣襄难以应对。就连他的老师欧阳中鹄也闻得风声,提出告诫:“吾弟此归专为经理家事,以尊府光景,根本不用担心家无余粮。你应该关起门来读书,涵养德性,宏阔志气,这才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事,不必纠缠于买贱卖贵,仿效那些商贩所行所为。”
谭嗣襄心绪难平,自认为在浏阳难以安身,便要抽身离去。他的性格与谭嗣同极为相近。性情中见筋骨,不移不屈,不失本色。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如此感叹:人生世间,天地必有以困之:以天下事困圣贤、困英雄,以道德文章困士人,以功名困仕宦,以货利困商贾,以衣食困庸夫。天要困我,我必不为所困。
这样的话听来像是谭嗣同说出口的,可见兄弟二人朝夕相处,有太多共通之处。谭嗣襄决意离开浏阳,自谋出路。他想要北上京师谒选,谋个实职,但又苦于缺乏经费。谭继洵一直没有给嗣同兄弟析分财产,只是每月给些定数的零花钱,也不多给。他们没有独立的生活来源,经济上完全依赖谭继洵,颇为窘迫。
这时,谭嗣同怀着悲喜难明的心情再次回到故乡。虽不免伤时感事,但见到仲兄谭嗣襄仍是最大的喜乐。回到浏阳,除了跟堂兄弟们把酒言欢,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仲兄身边。自从母亲和伯兄、姐姐去世,他和仲兄谭继襄本就亲近的距离拉得更近了。无须酒酣耳热,兄弟二人坐于书斋,纵情高论。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感情在岁月中的积淀一时得以宣泄。他们是血亲兄弟,也是世间知己。彼此不讲什么礼数,自由自在。梅花巷的东面有一片竹林,绿荫蔽天,其中生长的竹笋鲜脆可口。他们经常会走到这里,望着不远处的浏阳河,感叹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他们的父亲谭嗣洵总说,这个世道是公平的,有能力、有才学才可以进入体制内吃上一碗官家饭,有本事的人才能得到提拔重用。谭嗣同私下也与哥哥聊过,他们认为,吃上官饭,是一个人展示才能和本事的初始阶段。所谓的本事,不过是低级的奉迎之道,是人性卑劣的自然反应。而他们的父亲做不到,虽然有吃上官饭的才学,却没有混迹官场的本事。
谭嗣同和哥哥一次次走进考场,又一次次承受着榜上无名的屈辱。在这段时间里,兄弟二人不停地辗转于科场,就像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持心中之剑去迎接命运的各种挑战。可很多时候,这个世俗世界为他们安排下的“有物之阵”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掀开来看,从里面蹦出来的全是跳蚤。用一把心中之剑去对付一只只跳蚤,实在是说不过去。
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方大员,他们自然被体制内人士高看一眼,但其中苦涩的滋味只有他们知道。父亲像一座山,将他们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他们的路,是父亲道路的延续。他们是宗族血缘链上的其中一环,他们不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对于宗族来说,只是一个虚词。实实在在,又若隐若现。十一月间,谭嗣同告别仲兄动身前往甘肃,在陕西度岁,到次年正月才到达兰州。到达兰州后,他就在布政使署憩园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住了下来,潜心向学。此时,正值春雨连绵,房屋四壁长起点点青苔,雨水从破瓦缝里落下来,淋湿了屋中地板,外面廊阶也为积水所淹。尽管环境和气候不好,但他处之泰然,觉得这比跟着父亲和庶母住在一起要心情舒畅些。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羽飘零
- 我的爆乳巨臀专用肉便器王苗壮(LIQUID82)
- 糜烂病(gl骨)醍醐灌顶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季寒声沈清璇于春色暮晚相拥结局+番外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优雅迷人的金发大小姐奥黛丽和冷艳无口的木偶小姐莎伦被壮汉破处奸淫,最后双双恶堕为淫纹性奴凝夜紫
-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
- 都市奇缘易天下
- 直播也能挽救用品店吗啊若
- 无限之生化崛起三年又三年
- 高贵美艳的丝袜舞蹈老师妈妈(无绿改)江
- 在三无冰龙娘的诱惑战下逐渐染上败北射精癖的冒险者听雨
- 将警花妈妈调教成丝袜孕奴佚
- 可怜的社畜东度日
- 堕淫之魔法少女优卡莉茜娅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为了治疗丈夫的勃起障碍,只好和儿子上床的教师美母大龙猫dalongmao
- 黄历师石头羊
- 【黯的旅程】魔枪舞姬的初体验逛大臣
- 软香(1v1)h苏玛丽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甜秘密(校园高H)翼山明
- Kiss Me if You CanZIG
- 大奉打更人之佛陀的阴谋对酒当歌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江湖孽缘(修订版)红绳紫带
- 名义:人在军阁谁敢动我孙儿同伟好溪之澜2025
- 北电门房娱乐圈老司机
- 我有九千万亿舔狗金(系统帮我睡女人/系统帮我开后宫)番茄第一帅哥
- 四合院:我在四合院有个青梅竹马梦想车厘子自由
- 月明星稀月明星稀
- 亲爱的小孩(母子h)一条孤狼
- 我的卡牌后宫我想躺平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仙子的修行k
- 陈斌高婉君绯色青云陈斌高婉君后续+完结
- 娱乐春秋(加料福利版)姬叉
- 真搞熟妇亲人呸
- 二次元催眠调教日记月
- 仕途佳人仕途佳人
- 官路美人迎风笑
- 乱伦天堂黑
- 掌握催眠之力后的淫乱生活蘑
- 女神攻略调教手册明
- 月伴清风月伴清风
- 仙母种情录欢
- 明星潜规则之皇梦九重
- 我和淫乱后宫们的ntrs性福生活chuya
- 我在北电当教兽三修萨满
- 北境之王:穿越后被战神娇宠了+番外看风也听雨
- 裴总捡回来的小可怜,又疯又粘人酒酒子琪
- 快穿之打倒重生文女主露娜斯朵芮
- 谁家小鱼快来认领+番外云边鹤
- 仙子破道曲漆黑烈焰使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综漫同人)拜托你了,银时老师水云烟霞
- 上错暗恋对象的迈巴赫/只有烟花知道八月糯米糍
- 故旧新逢观然
- 头七见魂CPwinter酱的脑汁
- 婚内暗恋[先婚后爱]黎纯
- 鼎炉秘典:道途淫靡长生欲道
- 秋天不回来-我的教师美母江风夜话
- (综漫同人)完美反派就业中[综]天涯晨曦
- Re:从零开始的基沃托斯恶堕计划Arch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黑莲花今天也在碰瓷我薛不会
- (古典名著同人)孙悟空三打奥林匹斯山沈镜渊
- 我的学氓魅魔女友kkkf
- 快穿之差点被带偏了+番外爱吃花生酱烧饼的犰弘
- 男子高中生不会梦到阴阳双胞胎姐妹一盘没有梦想的鱼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梦中攻略室友她哥后,意外掉马宁昏
- 在ABO世界当牙医+番外乌衣祭
- (灵能同人)穿到老公少年时+番外流浪板栗
- 替身罢了,重逢为何不放手无极烟火
- 爱过,但我选权力枕上灯
- (天国大魔境同人)命运引领我走向你+番外流浪板栗
- 重演CP放野燈
- 月光彼岸CP+番外鱼粮姜烩
- 超可爱美少女是我妹妹我就是小疯子呀
- (灵能同人)去世后我又活过来了流浪板栗
- 白首与君同时间在看
- 死遁后我成了仙门白月光纯情母猪
- (少女漫同人)我的男友是邪脑科学家兔子饼干
- 国王的漂亮宠儿[无限]+番外清酒渍
- 快穿:恶毒女配真需要拯救吗+番外送花给你